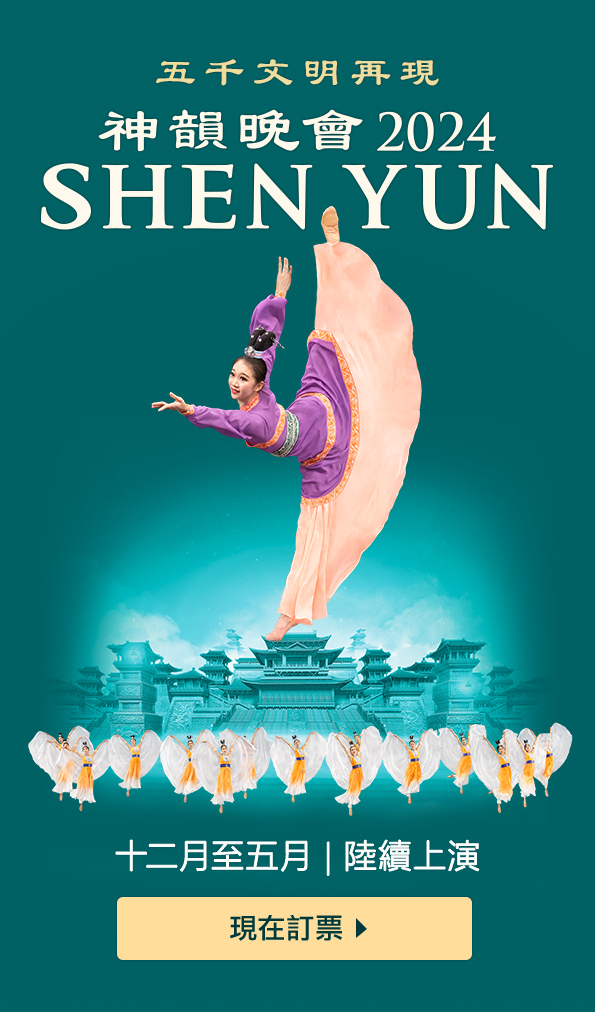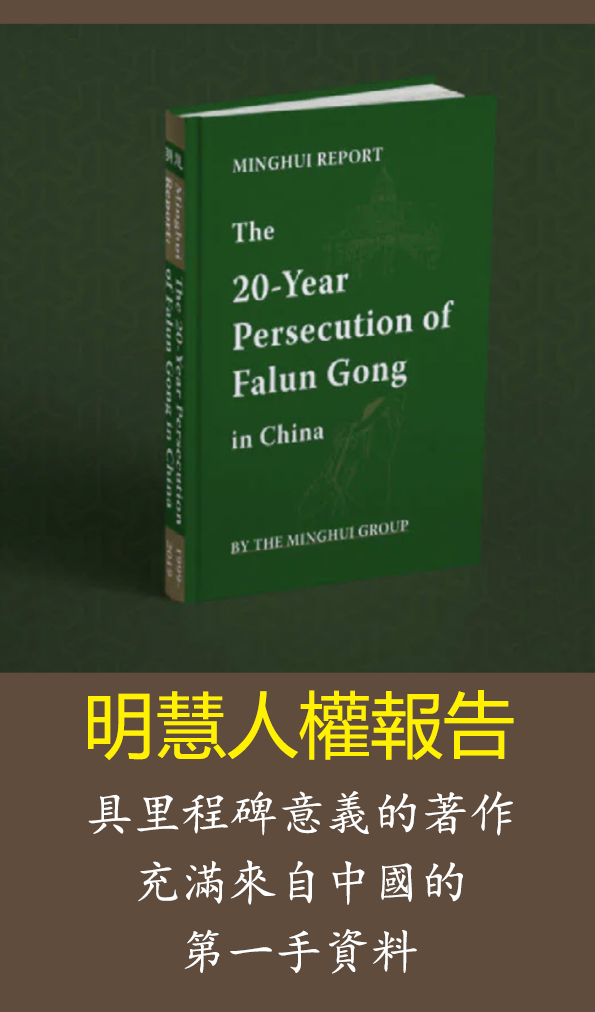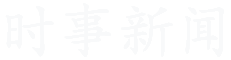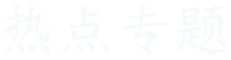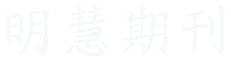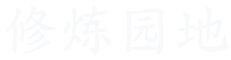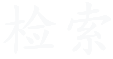我五年来在吉林市看守所和长春劳教所遭到的残酷迫害
第二次在1999年10月9日我和爱人又去北京找信访办说明法轮功是什么,还没有找到信访办我们就被不法人员抓了,警察把我们劫持到吉林驻京办事处,那里已经非法关押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天把我们劫持回吉林。在驻京办的时候,警察把我们的钱财抢劫一空,当时我有700元,爱人400元都被他们搜去了。
警察把我们非法送到了吉林市第一看守所。我们不承认有罪错,我们写上告信,要人权,政府不法人员这么做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每个人都有上访权,知情权,江氏这样是不得民心的。上访信,上告信我们写了,但不见回音,我就开始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为我们没有罪错,是迫害我们的人错了,他们在犯法。当我绝食到第八天的时候,警察想让爱人劝我吃饭,我告诉他说:谁劝也不好使。我不会吃的。就这样几天后,我被释放了。
1999年10月27日我们夫妻第三次去北京护法,火车上到处查法轮功,由于我们没带身份证,车到唐山时我和爱人就下车了。我们步行去北京,当接近北京时看到所有通往北京的路口都被封锁,进不去了,我们只好返回。刚到家,派出所和街道几个人闯入了我家,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我爱人被送到了看守所。
在洗脑班里,不法人员逼迫我写所谓的保证书,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写的,这样没过几天我被放回了家。1999年12月我到功友家参加法会,被别人告密又被抓入了第三看守所,在那里非法关押了36天。到期时也不知是哪来的人把我带到派出所让我写保证书。到中午12点多钟,哈达湾派出所恶警张寿斌把我提出来,在车上我向他们洪法。张让我把《转法轮》书交出来。我不会交的,他们就开车到我家把门砸开(砸门时张的手被铁锤震出血了,肿得象馒头一样)他们进屋就翻东西。我严厉的对他们说了几句话,我的坚定把他们震住了,他们态度马上变了,说你把身份证给我就行了,我好交差。
2000年3月2日我和几位同修又去北京护法,这是第四次。要求政府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我坐火车半途中被公安查出,把我们送到抚顺城车站,把我身上的钱搜去,共计305元钱。然后吉林市哈达派出所恶警张寿斌和我们单位的书记将我从抚顺接回,送入拘留所最后送第一看守所里。我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每天都炼功,十几个犯人蜂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用鞋底连打带抽,而且恶警管教邢淑芬体罚我蹲9个多小时,就这样我还是坚持炼功,恶警邢管教从别的号调犯人打我们,我心中想人在造业,她自己不知道,我就向犯人洪法、背经文。从那以后,再也不打我们了。
2000年3月我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入长春劳教所。在关押迫害我的大队,我写多少次复议书,起诉书,上告信,控告江泽民等等,不见音信。我想到做为一个修炼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炼功证实大法。我本着这样的想法炼功证实大法。犯人用皮管抽打我,而且把我的手脚用绳子绑上不让炼功。
有一个功友叫王素芹,50多岁,坚持炼功,被犯人打抽在地上,我们一看人躺在地上,没人管,犯人洋洋得意而走。我们说人躺在地上叫管教,不一会儿,恶警进来瞧一眼说,不管。我们开始绝食,在绝食中,我们每天从早晨干活到天黑。我绝食第六天时,中午开饭,我在一边趴着背经文《苦其心志》:“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最后王素芹的事解决了。
2000年4月28日我被劫持在四大队,我继续炼功,恶警于管教把我叫到管教室,让我写保证书。保证不绝食,不炼功,不传递经文。我回答:关于法轮功我不会签一个字的。恶警一听这么说,马上拿起手铐把我吊在床头,用电棍电我一阵,然后叫我签字。我回答:我没有任何罪错,不签字。
恶警转身出去,进来2个犯人,一来就打我几个耳光,还骂我。我心里背师父经文《无存》。这时恶警进来说等两天再收拾你。我开始绝食,恶警给我灌食,我不开口,就用一个铁器把我嘴撬开,往里灌食。胶皮管从嘴中插入胃里,当时呕吐不止。胃被盐水刺激得火烧火燎的。
2000年5月1日,四大队组织大法弟子看电视。这时全体大法弟子都起来炼功。管理科长岳君管教蜂拥而上用电棍电大法弟子。5月13日,被非法关押在四大队的大法弟子全体绝食要求停止迫害。不法人员把我们绝食的领到劳教所医院灌食,第一个给我灌食。
恶警把我绑在铁丝床上,手脚用皮带系在床边。有一名犯人摁我的头,开始灌食,这时恶警管理科长岳君手拿电棍象失控一样电我脖子和全身,这时我的身体被电的都弹起来了。电完一阵,把皮带解开,我下床走几步靠墙边,不一会儿,我昏倒在地上。
2000年7月劳教所开始强制洗脑转化,要求所谓的“百分之百转化”。这时恶警经常找我谈话,让我决裂,我不决裂。这时听到管教室传出一声声的惨叫,天天都能听到。队长张桂梅把我找到管教室问我决不决裂,我回答不决裂,然后就遭到一阵电棍。
2000年11月1日,恶警张桂梅又把我找到管教室逼我写决裂书。我不写,她拿起电棍就电我一阵。问我能不能写决裂书,我回答:不能写。她就把我关入了小号,把我的手和铁门栅栏铐在一起。这时我的手被手铐紧得周围都是泡,手肿的像个馒头一样,已经不能握拳头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老鼠在我身上乱串,当时老鼠几乎爬遍了我的全身。
在这期间不准我刷牙、洗脸,一天上三次厕所。恶警袁影还是经常的威胁我,逼我写决裂书。恶警袁影对我说:如果你不写决裂书,让你一辈子呆在这里。当时叛徒犹大也一直劝我写决裂,我心里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
直到有一天,我悟到了要离开小号了。第二天一大早恶警袁影就用那恶狠狠的声音把我叫出去。而且恶警对我说:你不决裂每月都给你加期一个月。2001年3月我被分到三小队。
2001年5月我10岁的儿子,由于一年多没有见到母亲,思母的心切。有一个写了决裂书的人刘秀珍给劳教所恶警张桂梅打电话,让我们母子相见。这时恶警张桂梅心中想出用儿子逼我决裂的狠毒方法。恶警张桂梅说:看你儿子的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你见面,这才让我接见了自己许久没有见到的儿子。于是带着孩子同来的(舅妈和姨)都对我说:她们都不开工资了,都下岗了,照顾不了你家的孩子,让孩子跟我一起在劳教所里,她们不管了。我对她们说:我这也是逼不得已,孩子身边的父母都在劳教所里。孩子除了你们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如果你们实在不想照顾孩子的话,就把我家中值钱的东西卖了,把孩子送入孤儿院吧!恶警张桂梅一听我这么说话,转身走了。没多长时间,恶警张桂梅把我叫到管教室就是一阵电!接着恶警殷队长和关微又电我一阵,逼迫我决裂。我不断的喊着:你们就是电死我!也不会决裂的。
2001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干活,同修上厕所时听到电棍响,对我说:恶警又在电大法弟子刘庆杰。这时又听说李永军被关入小号。我想大法弟子整体,今天迫害她,明天迫害我。我开始绝食,我被恶警叫去,刚入管教室,恶警刘志伟动手猛打,问我为什么绝食。恶警大队长关微用电棍电我的头部,当时就把我电倒在地。恶警一看,这样给所打电话灌食,我的鼻子被管子插的直流血,插不进去,最后对嘴插管灌。过几天,恶警找我谈话,我说把关押在小号的大法弟子放出来,我就吃饭。恶警说我们放人了,我一看小号没有人。然后恶警把人领出来让我看,我就吃饭了。
2001年11月我被加期9个月,在四大队挑豆子,我和厂家的人在一起挑豆子,我就向厂家的人讲真象,我说炼法轮功的人,有的得很重的病,到医院看不好通过炼功病都好了。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不让炼,群众去北京上访,把这些好人抓入劳教所,采用流氓手段迫害大法弟子,有的被害死,有的被打残废的等等,我说了很多。这时有一名决裂的人姜秀芹哭着说:“谁愿意决裂,都是不情愿的,自己承受不住,违心写决裂书的。”这时厂家的人虽然不吱声,但是他也在听我们讲。在劳教所里,我们能接触到的常人就向他们讲真象。
由于我不改变自己的信仰,被非法加期迫害300多天(近10个月)。2002年1月22日,我从劳教所里堂堂正正的走出来。
当我回到家时,由于邪恶的迫害,丈夫流落在外,我与孩子在家生活。而哈达派出所恶警到我家骚扰我正常生活,而且连我的亲属都不得安宁。由于恶警抓不到我丈夫,好心人对我说,恶警到学校抓我11岁的儿子,两次没抓着。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孩子失学。我一看这个家,我实在住不下去了。被迫带孩子流离失所。
2002年6月18日我骑自行车到功友家去取《转法轮》。(功友租的房子)刚拿钥匙打开房门,眼前站着三个人,把我拽入屋里,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看到屋子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
不法人员把我劫持到派出所,非法提审我二个小时,我就是一句话,取《转法轮》书。这时恶警刘所长对恶警说,别跟她们废话,然后把我领到别的屋,把我身体呈“十”形绑在椅子上。又过来一个恶警(姓刘,脑门上有一绺白头发),提审我,我一言不发,用台球棍砸我的脚趾盖,随后用台球棍点我的喉咙,看我还不说,就打我几个耳光。这时恶警刘所长进屋又问我,看我还是不说,拿起电棍就电我。
我心里就不停的发正念,过一会儿,恶警刘所长不电了,对我说别人都把你供出来了,你还嘴硬。恶警转身出去把同修领到跟前,问同修:“你认识她吗?”同修说:“认识。”然后同修对我说,该说的就说吧(希望这位同修更够认识自己犯下的出卖同修的大错,加倍弥补),我一听没吱声。
恶警看我还不说话,把同修领出去了。然后,就问我:“这几个地方的经文是你送的吧?”我还是不吱声,恶警转身出去了,又进来一个外号叫法西斯的恶警提审我,对我说:看来你要吃苦头了,恶警问我进屋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取《转法轮》书,恶警拿塑料袋就捂我的头,捂好长时间才把塑料袋摘掉,还逼我口供,我还是那句话取《转法轮》书。恶警一听还是那句话,又对我说再给你加两个塑料袋在一起,让你尝点滋味,然后第二次又捂我的头。
当时我被恶警捂的都要窒息过去了,眼前发黑,心脏就象要蹦出来一样,脸憋得很青。恶警一看我不行了,把塑料袋摘掉了。然后继续逼我口供,我还是那句话,取《转法轮》书,恶警象发疯一样,连续不断的捂我三次到四次。我心里想,我是神,能怕恶人吗?我对恶警发正念,紧接着我讲真象。我说大法弟子在救度世人,告诉世人做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可是江××害怕好人多,把大法弟子都抓入劳教所、监狱等等,大打出手,把你们当做他的工具使用,真的把你们给害了。我说你千万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我一直在讲真象,下午2点多钟不法警察把我非法送入第一看守所。
2002年6月24日不法人员又把我非法送入长春劳教所,开始对我洗脑帮教、体罚。
2002年7月,四大队放天安门自焚录像,把我也叫去。四小队都谈谈自己的认识,我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自焚事件是国家瞎编的,编好的镜头放出来,大法弟子只是把镜头放慢了,让世人看清楚自焚过程中的很多疑点。第二天叛徒犹大孙树芹等人报恶警刘志伟,随后把我叫去,恶警刘志伟拿起电棍就电,正在这时恶警大队长张桂梅逼迫我吃药。我不吃,恶警张桂梅上去就给我一拳,把我的嘴打出血来。恶警刘志伟逼我决裂,说你就写一张决裂书就可以,其它的书不用写。我不写。叛徒犹大成宿不让我睡觉,体罚帮教。
我对大法的正信,谁也动不了我的心。叛徒犹大又采用新的办法,把写好的决裂书让我签字。我不签,蜂拥而上、七、八个人上来就把我摁倒在地上,有摁头的,有摁腿的,还有拽着我的手的,把犹大写好的决裂书让我摁上手印,我不摁,心中在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邪恶黑窝点迫害我,大声喊:“救命啊!有人在迫害我。”
这时恶警王晶管教过来就用麻布把我的嘴给勒上,拽着我的手就往决裂书上摁,用强制的办法对待我,不好使。我马上站起来说:“你们什么也别说,把决裂书给我。”这时我对犹大发正念,然后我心想为了犹大清醒少做恶事。七、八个人把我摁倒在地,其中有一个人叫李志兰没动手,犹大都说:大伙都摁杜洪芳,你为什么不动手。李志兰哭着说,我决裂时,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对待我,我不想用这种方式对待杜洪芳,我看到这一切,我就想起自己决裂的场面。我下不去手。
没过几天,我看墙上贴出写大法不好的标语,我想起师父说的“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等到半夜我就给揭下来撕了。第二天恶警刘志伟给我找去,又是一阵电棍。恶警刘志伟说: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写思想汇报,送到管教室给我。第二天,我把思想汇报送给管教刘志伟。恶警看完后,就是打我几个耳光,然后拿起电棍电我一阵。一连八、九天都是这样对待我。最后我不写了。恶警刘志伟看这招不行,又使出最恶毒的办法。二小队全体开会,恶警刘志伟说:只要杜洪芳不决裂,你们谁也别想减期;二小队36个人,35人决裂,难到一个杜洪芳还“帮教”不过来。我心中发正念谁迫害我,我就对谁发正念。帮教我时都上厕所。
2004年6月18日我两年期满,恶警多次找我谈话,逼迫我写保证书,放我回家。我不写保证书,恶警就要给我加期。我想起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
我回答:没有任何保证。后来恶警又给我加期30天,这次一共被加期40天。我被非法劳教要到期时,恶警刘志伟找我谈话时要求我别给上网揭露劳教所恶警的丑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