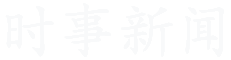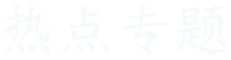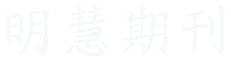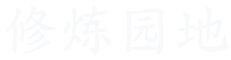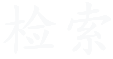坚信师父和大法,做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
3. 天安门证实法
在本地很多学员能够走出来证实大法后,我想我也该去天安门证实大法了。在当时极其邪恶的环境下,谁都明白去了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刚到外地生活不久,人生地不熟,临行前,我的家人求着我:万一有什么事,小孩还小,这个家怎么过下去。我讲了很多道理,为了不牵连她,我写了离婚书,叫她带着小孩回老家去。第二天,我从同修那里借了钱,带上手提包,里面装上《转法轮》和《精進要旨》,离开了当地。
当时全国各地去北京的路都受到邪恶的严查。在郑州汽车站,刚上车就有几个便衣来查问,他们叫我拿出身份证,问我从哪里来的,去哪里。我沉着地回答,他们看了我一会儿,就把身份证还给了我。到达北京已是下午,本来一位学员曾给了我一位北京学员的传呼号码,但走之前我的电话本被家人藏起来了,我只大概记得机主号码,传呼台号码记不清。于是我向着天安门的方向走了很远的路,一边走一边想,同时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希望能与北京同修联系上,如联系不上,我打算第二天一个人就到天安门去。到了北京西客站,我“突然”想到买一份晚报来看,也许能找到传呼台号码,果然有一个号码我觉得就是,我马上拨了传呼,等了一会儿,回电话了,我们联系上了。到达北京学员那里时天已经黑了,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我们却一下就认出了对方。当时北京学员被看得很严,到处有警察、警车在巡逻。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很快到了一个安全地方住下来。
已有几位东北的同修先到那里。在随后的几天里,陆续从全国各地又来了许多同修聚在一起,已经有四、五十人了,我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一起交流一起学法,度过了几天难忘的日子,虽然同修们都是第一次见面,但却感觉很面熟,因为我们都是为法而来,而今天又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维护大法、证实大法走到了一起,实在是太难得了。我还利用这个机会与北京的一些同修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从黑龙江来了一位同修,他是一位公安,住下来后有同修反映他对法不是很熟悉,大家一下搞得比较紧张。后来证明这都是我们的心不纯造成的。由于已有一个点的几十个同修被公安发现后抓走了,当时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商量后大部分同修转移到了其它地方,自愿留在这里的有十来人,我与那位警察同修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也是带着目的想探探他的具体情况(其实这样做也有不对的地方)。他很朴实、不太会讲话、没有豪言壮语、但对法却有纯朴的心,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想起当时的情况我还常常内疚他当时要承受多大的来自学员不信任的压力。由于99年7.20前夕的部分经文和以后的新经文他都没有看到,确实在学法上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把随带的经文给了他,以后的两天,我们就在一起集体学习《转法轮》和新经文。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直到天安门广场。临去前,他还问大家,该不该穿着警服去天安门,大家认为我们应该以各自人的最能证实大法的一面去证实大法。后来他穿着警服走上了天安门。
早上8点多,我们来到了天安门。由于邪恶集团害怕7.20到来之际出现大法弟子到天安门大规模的诉冤请愿,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很多的警察、便衣和武警,沿着广场四周,大约2米就有一个武警,当时已处于半戒严状态,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入广场。很多大法弟子还是利用各种方式走进了广场。
进入天安门广场后,我们在广场中间找了一个地方,等着时间一到大家就一起打开横幅。那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来了,您为弟子们受苦了。当时,广场上已有数百名大法弟子。9点钟,我们迅速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大横幅,我们打开横幅,一边跑动一边不停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是啊,那是心灵深处最真诚的呼唤,那是为了真理舍尽一切的正义呐喊,那声音响彻了宇宙,震撼了苍穹。面对蜂拥而至的暴徒警察,我们高举着横幅,哪怕只要能够多举一秒钟,我们都在坚持着,那时的每一秒,都意味着有数不清的拳头和警具打在我们身上,直到最后,我的头被打得一片空白,嗡嗡直响,被打倒在地上,它们打的打,踹的踹,当时已不清楚那些暴徒是怎样把我使劲按在了警车的脚踏板上,这时脑子才回过神来。被暴徒打上警车后,我看到有好几个暴徒还在打那位警察同修,他的鼻子被打出了血,鲜血直流,几个警察把他也打上了同一辆警车。在车上也有几个警察,其中一个还拿着搅动汽车发动的那个铁拐子,挥动着要打大法弟子。
很快,我们被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我们没报姓名,就被编了号临时关在停自行车的后院里。那位警察同修刚一到天安门派出所,那些恶警气得要命,说警察也为法轮功来了,于是粗暴的把他拉到一边,强行扒掉了他的警服,我在旁边喊到不准打人,它们就把我赶走了。很快,停车棚里装满了几百名大法弟子,再后来的就被关在地下室里。一个警察还叫嚣着要拿一挺机枪来。这时,我才看到我的手在流血,我的头、手、背等好些部位也被恶警在广场上打伤、打肿、打出了血。其他同修也是一样,好多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到处是伤,有的鞋子被打掉了只好光着脚,有的衣服被撕破了,我的眼镜也被打掉了。我们在那里高声背诵师父的经文和《洪吟》,从上午到下午,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就这样一篇一篇地、一刻不停地高声朗诵着,那情景真如排山倒海、气壮山河。这时,天奇怪地下起了一阵雨,一大滴、一大滴稀稀疏疏地慢慢地往下落,当时我感悟到,那是神在掉泪,他们真的被感动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感人肺腑、惊天动地的殊胜壮举,他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真正能够做到为了宇宙真理而放下生死勇敢地走出来维护大法、肩负起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每当想起那一幕幕我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约下午2、3点,后院的大铁门被一大群恶警打开了,它们狂叫着并动手要把男、女同修分开,打算先用车把女同修拉走。我当时正好在最前面,我们说不能听它们的安排,我们高喊:我们没有犯法,我们没有罪。那些警察蛮横无理地叫嚣:江××就是法律。我们手挽着手,不让它们拉走,它们开始使用暴力,一个武警先来拉我左边的一位小女孩,并动手打她,一个好可怜的小妹妹,她当时那种痛苦无助的望着我的眼神,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不让它打,我大声说:一个小女孩你都下得了手去打。它们又恶狠狠地转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一个警察抓住我的一大把头发使劲扯,一个恶警还猛击我的头,后来我被打上了一个大客车。就这样,同修们被强行分开到了不同的地方。我被拉到了北京的一个看守所。
4. 监牢里的迫害
到那里后,我们被拉去审问。在审问中,同修们基本上都不配合它们的提问。审问我的是二、三个年青人,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真实情况和我炼功受益的体会,大概是他们看到我身上很多地方有伤,并没有对我动粗。后来,我告诉了他们,我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和我的姓名。他们听了显然有些震惊,他们说,你是博士你还来,而且你还是学的那么好的专业。我说,我是博士都在炼法轮功,你们更应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应该以我在人间的这种高学位形式去证实大法。
北京的看守所是江××邪恶统治下的人间地狱,苦不堪言。我被非法关进了底楼的一间仓室,一个小铁门里面是一个约20平米的房间,一个小灯泡亮着,很昏暗。里面一张大木板,占了约十分之八的地方,那是十几个人睡在一起的床,有一个几十厘米宽的过道,厕所在进门的另一头,后面有一个小天窗,这是唯一能见光通气的地方,里面关押着十几个犯人。
刚一进门,牢头们就开始了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叫我法轮功,首先大牢头叫我头背伸直紧靠墙壁蹲着,并开始问话,动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或者声音回答小一点,或者回答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是拳打脚踹扇耳光,大牢头、二牢头、三牢头……一个一个的来。二牢头在“审”我的时候,盯着我看了很久,没有出声,他说出了一句良心话:“看着你真善(老实),我都不忍心打你,你知道吗,是警察叫我们打你们法轮功的”。后来三牢头找岔打我,一边问我,一边将牙刷的一头拉开用其反弹力不断的弹打我的额头或用牙刷来刺我,他纯粹是找岔发泄监牢里的苦闷,大概有数十下后,我横下一条心不理他了,看他怎样,他把我拖到厕所边一阵暴打,脑子一下给打得没有了知觉,大概是大牢头担心打死人,他叫人过来解围。那一天是又饿(没有给饭吃),又渴,又被多次毒打,又有伤痛。到了晚上,牢头不准我睡木板上,就只有在又脏又烂的土地板过道上迷迷糊糊地就昏睡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被几个犯人弄我的鼻子给搞醒了,原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呼吸已经死去了。后来,大牢头叫两个人不准睡觉,看着我。由于北京的恶警和监牢里犯人的毒打,不知是谁将我的左边肋骨严重打伤(因看守所医生不给检查,不知是否打断),剧痛难忍,每呼吸一口气就会牵扯得剧痛,睡觉不能压,转身不能碰。后来的一两年都一直隐隐作痛。
在监牢里,犯人们由于长年累月的被关押,在江××灭绝人性的虐待下,他们的性格都被扭曲了,他们想着方的以整人打人来发泄和打发时间。那里每天吃两顿,每天每顿都是一样的没有油水的几片茄子煮的盐水汤和玉米窝窝头,由牢头发给大家吃,一般情况下我能分到一小碗汤(这算是较好的对待了)和两个小窝窝头,有的犯人还经常吃不到就只有挨饿了,我常常有意省下一些汤,悄悄给最受他们欺负的一个犯人,在那里没有牢头的许可是不能公开把这一小碗汤私自分给别人的,他们常常打他,不准他睡觉,也不准他与其他人说话,我有机会就告诉他,叫他默念“真善忍好”,他会意的点头同意。
尽管一般犯人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牢头与看守所警察勾结起来过的却是另一番日子。在我被非法关押进去时,看守所的警察(个子不高约1.6米,50多岁)要我交出所有的东西和钱,并进行了登记。不久,牢头就来逼我拿出那些钱来,我说在警察那里拿不出来。他们说,他们知道我在那里有多少钱,他们有办法拿出来,但却要强迫我去签字领出来,原来他们早就同那里的警察勾结好了。有一天,牢头带着我到管收钱的那个警察那里,“自愿”签字把我的钱取了出来,马上就被牢头全部拿走了。一到晚上,他们几个牢头就买来酒菜大吃大喝起来。
但是,牢里的这些犯人很多还能够理解法轮功,他们还能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迫害,有的也认为终有一天会平反。很快,他们不再对我进行打骂,有时牢头还好心的主动叫我到那个监视器看不到的地方去炼功。
一天,看守所的警察突然通知我,当地驻京办来人要把我带走。一出牢门,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北京公安在门口,好像他们叫他什么局长?他问:还有什么东西吗?我说:没有了,都被犯人抢了。他马上为那些犯人和警察开脱,说没有这种事。后来他说:你是博士你还敢来,抓你个典型,再来把你枪毙了,同时手还比划着动作。被当地驻京办接走后,被非法关押在驻京办的一个地下室里,已有很多同修被先关在那里。第二天,我们一起被戴着手铐押上了火车,我们就一直被非法铐在火车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一个吃奶的婴儿。来来往往的旅客们,都在惊奇怎么铐了这么多人在车上。
在押回当地后,警察骗我说单位领导马上就来接我回去。一会他们却把我送进了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一位认识我的警察对我说,这次它们准备长期关押我。在那里,虽没有肉体的毒打,但却是更加摧残折磨人的苦役和精神迫害。
当时我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仍然是连呼吸都会牵扯得剧痛,而且头也很痛,但我死撑着不叫一声痛,也不掉一滴泪。尽管在天安门时警察把我的眼镜打掉了,视力很模糊,在严酷的迫害下没有人来同情你,每天仍然被强迫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要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工,日复一日没有周末,也没有工钱,这让人联想到小时候上学时在课本中描写的,“……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受尽了剥削”,我想,在这里的情况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看守所里是做一种彩灯,全部手工操作,一位牢头有点夸张的说过,东南亚的这种产品都是这些地方(注:指看守所等)生产的。很多人的手都磨掉了皮,缠了一层一层的胶布。我的手在做了一段时间后就麻木了,在以后的一两年里几个手指尖都没有知觉,使劲掐都感觉不到痛。
在那里有一件令人难忘的恐怖行为。有一天,大家正在做工,监仓的铁门大响一声打开了,突然冲进来几个手持武器的武警暴徒大叫着、狂喊着,那声音之恐怖如同从地狱发出来一样的令人毛骨悚然,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是怎么回事,它们已迅速把所有的人推到一个墙边,大喊把手放在头上,敲打着大家低头并蹲下,还个个搜了身,接着,那几个武警暴徒从床板到柜子,从衣物、被子到用具,一切东西,一阵稀里哗啦的全部翻乱,随处乱扔,一片狼藉,其行为完全是一群没有了人性和规矩的畜生,当时那恐怖的气氛和景象就跟电影里一场战役后的一模一样。这就是它们所谓的例行检查。等它们走后,我们才一样一样地到处去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再把它们放回原处。
除苦役外,最难受的就是精神折磨了,它们要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四年多来,江××一直利用整部国家机器的暴力和谎言来摧毁上亿民众自由选择锻炼身体的方式,剥夺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信仰,和自觉去做一个好人的天赋权利,这是古今中外再恶毒的邪恶之徒都不可能做出来的,因为那是一个人最最基本的天赐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无权去剥夺。在关押时,家庭、单位、公安等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来,有人给我讲过:因为我有很高学历,有特殊身份,有些人想借此“立功受奖”,要么彻底“转化”,就向X博士那样上报纸电视为它们作宣传,要么就重重处理长期关押。
当时我感到最让人难受的还是无法炼功学法,最最想要的就是能看到法。每天,一边做工,一边背着能记住的法,《论语》是背得最多的,不知道一天背了多少遍。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该讲的都讲了,那里不应该是我待的地方,心里升起了要想办法出去的心,而且,由于不能学法炼功,加之身体上的伤害,我感到头开始发晕,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就尽量打起精神保持清醒。最致命的是,我竟然忘记了向师父求救。
自修炼以来,我基本上都能做得较好,个人修炼的大关大难基本都能过去,还能在学员中起到一些好的影响,同时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培养了比较强的毅力和忍耐力,而这有好的方面,但我却没有深刻的向内找一个根深的变异因素,我以前总是对哪些过关过不去的同修感到不太理解,我也总是说,不要师父再为我们受苦,一切我们要自己去承受。长期以来,在我没有意识到的内心深处埋藏了一份变异的妄自尊大的心,潜意识里还认为自己就是了不起,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恰恰这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已经很难再承受下去了,我却忘记了向师父求救,还在用人的一面强撑着,加上一些没有修去的不好的人心,我还是用人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切,这就必然促成大错。所以后来,一方面我想绝不能让它们“立功”的阴谋得逞,我拒绝了它们的一些要求,同时我就敷衍着违心地写了认识和检讨等,在其中我玩着文字游戏,写模棱两可的话,同时,我发念(当时还不懂发正念)我违心写的材料在几天后自行销毁,我也对一些关键的词语发念注入真正的内涵等等;另一方面,我也横下一条心,如果它们要判我长期关押,我绝不认可,在某月某日之前如果不放我出去,我就死给它们看,我是被它们迫害死在那里的。后来的情况是在那个时间的前两天它们放我出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