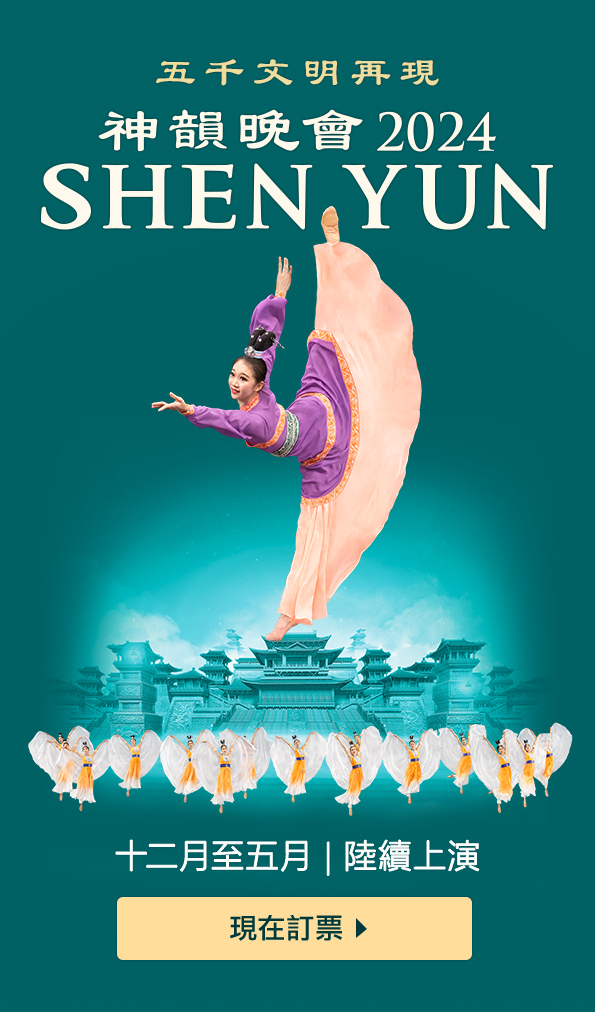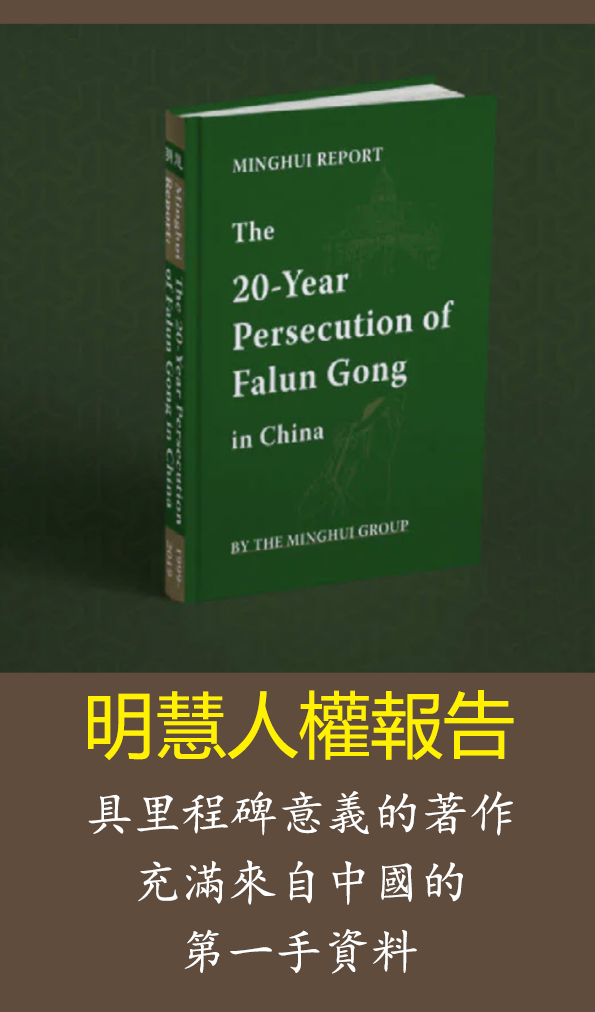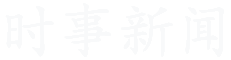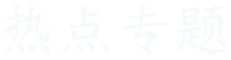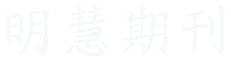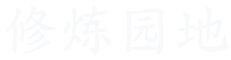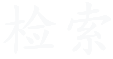在马三家遭受的肉体和精神迫害
“我被强行拖到综合楼小号,下午几个恶警把我连铁椅子一起抬到另一个小号。第三天小号队长打开扣手扣脚的锁,又把我扣在了又一个号的铁椅子上。我的双手、胳膊、脚、腿都肿了,左肋处也非常疼,我开始绝食了。”
“恶警黄海雁和张春光抓住我背铐的双手,两人拖起来就往外跑,拖跑到一楼楼梯一半处,两人把手一撒,我从楼梯上一蹬一蹬的滚了下来,滚到底趴在地上。两个恶警赶上来拖起我就往外跑,到门外转化者也帮忙往外抬,一直抬到晾衣场,强行把我铐在了晾衣场的铁管子上冷冻。”
这是辽宁省凌源市大法弟子周雅娟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遭受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迫害的几个小片段。下面是周雅娟自述其遭受的一些迫害经历。
我叫周雅娟,辽宁省凌源市人。1999年正月喜得大法,由一个体弱多病、厌倦人生的弱女子变成了一个身强体壮、明白了人生真谛的修炼者。自得法之日起,我在繁忙之余就是学法炼功。谁知好景不长,1999年4月25日后,不断的受到乡、村干部骚扰。2000年夏,乡派出所非法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炼功带。同年秋季,村民组长拿着一份转化书到我家,当时害怕迫害,违心的签了名。2001年正月十三,乡派出所再次非法抄家,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所长王立江把我的围巾拽下扔到床上,狠狠的打了我一个嘴巴。副所长裴仁把我带到所长办公室,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打到床边,刚起身又被踢倒。所长王立江揪住我的头发吼道:“你是金子吗?”不管他们怎么逞凶,我还是没签字。当晚恶警把我和李树英铐在一起绑架到凌源市拘留所。
在凌源市拘留所,由于超期拘留,被非法关押的全体大法弟子联名向所里递交了上诉书并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还大法师父清白。谁知我们十余名大法弟子被一群打手强行拖上警车送进凌源市第一看守所,十八天后被送回拘留所。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后,我被非法判处三年劳教。于2001年6月7日我和另外9名大法弟子被凌源市公安局绑架到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现改名为所谓的“思想教育学校”),一直非法关押在女二所一大队三分队,队长是恶警黄海雁。在那里我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时刻都受到非法监视。
刚到马三家时间不长,那时还在老楼(男六队旁边)。一天室长说队长找我,我到了队长寝室。恶警黄海雁问我:为什么不背三十条?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有师父的法作指导,知道怎么去做。她又说我不管孩子,我说:不是我不管,这一切都是中共江××政府造成的。恶警黄海雁照我的右胸猛的打了一拳。
大约7、8月的一天,马三家教养院强制全体大法学员打一种不知名的针。我不配合,当天被洗脑的人骗到楼下,一进屋看见几个恶警和几个转化者摁着坚定的大法弟子王荣红(大连人),要强行打针,我冲上去阻止又被转化者拽住。她们又把我强行摁倒在地,往下拽我的裤子,我和王荣红都被强行打了针。
2001年11月29日,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全部迁入新楼,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12月的一天,由于不“上课”,恶警黄海雁指派两个转化者在室内给我念攻击大法的书,她俩把我堵到墙角轮流大声念。我大声背论语,发正念,她们边念边用手比划。我忍不住抢过书就撕,她俩往回夺。这时也下课了,我被几个转化者拖到队长值班室,恶警黄海雁照我的右脸猛的一拳,打得我头发昏,差点摔倒,恶警王淑征(干事)照我的左胸狠狠的一拳,恶警张春光(一大队五分队队长)、任红赞(六分队队长)使劲掐我的脸、脖子,四个恶警把我堵在墙根,折磨一阵后又把我带到一楼,恶警黄海雁和几个转化者强行把我铐在一个监号的床边,她们夜里又把我铐在长条椅子上冷冻。当时王荣红、杨景芝(朝阳北票人)被恶警分别铐在别的监号里。回室后我给省法院写了一封上诉信,被恶警黄海雁扣留。我和刘艳文(辽阳人)由于不做操,恶警黄海雁指使转化学员做我们的“工作”,并扬言铐到楼下冷冻。针对此事当天夜里我给中共省委书记闻世震写了信,又一次被黄海雁扣留。
2002年,一天恶警黄海雁把我们几个坚定的大法弟子骗到食堂外,企图做所谓的“转化工作”。王荣红被骗到综合楼,我和杨景芝、刘艳文不听恶警分派,先后被连拖带抬到晾衣场。我不听转化者的谎言,她们向队长汇报了。恶警黄海雁随后把我铐在了晾衣场的铁管子上,下午见我还不配合,于是他把我的双手背铐,又找来一个长条宽布带,几个恶警狠狠的把我的嘴勒住,几个转化者把我弄到一楼,关进二大队的库房里。站着怕别人看见,又找来小塑料凳强制我坐,我不坐,他们使劲按我。恶警黄海雁又使劲勒我的嘴,我只觉得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身子往下倒。
昏迷中听到恶警黄海雁说:“不行了,死了,死了。”她们用手扒我的眼睛,渐渐的我睁开双眼,只见转化者和恶警黄海雁蹲在我的旁边,她们见我醒来,一转化者搀着恶警黄海雁的胳膊说:“走,别管她!”只留下一个转化者看着我。
我吃力的用舌头、嘴唇把勒嘴的布条一点点的弄下,过了一段时间取货的厂家来看货,转化者急忙把手铐钥匙找来给我解铐。晚上看我的人叫我吃饭,我说嘴都勒破了怎吃呢!她叫我张开嘴看看说:“嘴唇里都勒出泡了。”晚上恶警黄海雁又把我铐在了值班室的暖气管上。第二天上午,大队长王晓峰把我放回了室内。
5月份的一天中午,恶警王晓峰和黄海雁到我的室内翻东西,同室别的人都去食堂吃饭了。由于我们不穿校服,不允许去食堂吃饭,都是学员吃完后带饭回来。〔王荣红被恶警黄海雁送进小号,60多岁的张云霞(铁法人)长期被关在一楼〕恶警黄海雁翻到了杨景芝的一个日记本,里面纪录的是她到马三家遭受的迫害及见闻。恶警黄海雁一边撕一边说:“我叫你写,我叫你告,有能耐你告呀!”随即又来几个恶警,我们三个先后被拖走。我被拖到队长值班室,铐在了暖气管子上,恶警黄海雁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我的头。此时学员们吃完饭排队回来,恶警们怕学员看见赶紧把门关紧,学员们走完后黄海雁和几个恶警强行把我拖走。男恶警郭方杰把我的左胳膊往后一拧,说:“我来拖!”我被强行拖到综合楼小号,下午几个恶警把我连铁椅子一起抬到另一个小号。第三天小号队长打开扣手扣脚的锁,又把我扣在了又一个号的铁椅子上。我的双手、胳膊、脚、腿都肿了,左肋处也非常疼,我开始绝食了。在小号队长的反复劝说下,两天后我又吃饭了。第七天恶警黄海雁到小号问我穿不穿校服,我说不穿。又在小号扣了十一天。回室后,才发现我的上衣被恶警拉扯出好几个口子,是刘艳文帮我缝上的。我手肿得连衣服都洗不了。
又一天的早晨,由于不穿校服,一个转化者说队长找我,我说不去。时间不长,恶警黄海雁领着几个转化者气势汹汹的来到室内,强行把我按倒在地。恶警黄海雁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地往地上摔我的头,十来个人拧胳膊、按腿强行给我套上校服,后又把我拖到队长值班室,铐在暖气管上。恶警黄海雁揪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我的头。早饭前,又把我拖到综合楼小号,扣在铁椅子上,右手、胳膊连拧带扣的肿得十分厉害,吃饭、上厕所都困难。第四天夜里我要上厕所,小号恶警不让,我憋不住尿了裤子。隔壁小号关的是由于写上诉书而遭迫害的李冬青,她先是在一楼被铐了二十多天。一天夜里恶警们又强行把她抬进综合楼小号,都两个多月了。8月22日上午,我被放回室内,李冬青、李莉明、宋彩虹三位坚定的大法弟子在非法审判大会上被批捕。
10月份,马三家教养院大部份学员被迫去地里扒苞米,每年都是如此。一天副所长王乃民见我们不去参加劳动,指使几个恶警和四防人员把我们抬上警车拉到苞米地里,我们不配合非法劳动,恶警王乃民把杨景芝弄走,恶警王晓峰罚我和刘艳文蹲着,学员们扒了半个月苞米,我和刘艳文在地里蹲了半个月,60多岁的张云霞在地里坐了半个月。晚上学员们睡觉后,我们三人还被迫到水房站着。张云霞站不住了,坐了几天回室了。我和刘艳文站到十二点,最后几天都站到后半夜一点。杨景芝原来被关进了小号,回来后她对我说,恶警王乃民说就欠把她扔进男监。由此我想起了十八名女大法学员在马三家被恶警扔进男监的事。
有一天不出操,我被几个转化者拖进队长值班室,强行铐在暖气管上。大家们出操回来后,恶警黄海雁和几个转化者把我往综合楼拖,拖到小号铁门外,恶警黄海雁把学员们撵回,把我扣在小号的铁椅上,整天播放攻击大法的高音喇叭。一天三顿窝头、咸菜,只让上两次厕所,真叫人难挨!我又一次尿了裤子。恶警黄海雁说我肾有毛病,叫我吃药,我说我没有病,来马三家时在医院体检都没毛病,是你们迫害的,我不吃药。恶警黄海雁、小号恶警杨队长和一名小队长强行给我灌药,恶警黄海雁找来一小块木板,狠劲撬我的嘴,嘴唇被撬出了血,墙上也弄上了血,擦血的卫生纸用了一大堆。恶警黄海雁见实在灌不下,就气呼呼的走了。小号恶警杨队长对我说:“我觉得我够狠的,黄海雁比我还狠。”这次我在小号里被扣了二十多天才放回室内。
11月份的一天,多数人去食堂考试,室内只剩下我和杨景芝、刘艳文等几人。大队长王晓峰来了看看说:“你们就这么坐着。”不一会,恶警黄海雁来了,叫我到床脚处坐着,我说:“刚才大队长来叫这么坐的。” 恶警黄海雁说:“我就叫你上那坐着!”说完抓起我的衣领就往外拖,一直拖到厕所,一阵拳打脚踢。我被踢得在地上滚来滚去,一会儿她打够了,扬长而去。我慢慢的爬起来,吃力的挪回室内。还没等坐稳,恶警黄海雁和王晓峰又来了,她们再一次把我拖进厕所双手背铐,踢的踢,打的打。一阵毒打之后,又把我拖到队长值班室,扔在地上。恶警黄海雁眼冒凶光,狠狠的踢我的脸、下颏,又叫来一转化者,恶警黄海雁和张春光抓住我背铐的双手,两人拖起来就往外跑,拖跑到一楼楼梯一半处,两人把手一撒,我从楼梯上一蹬一蹬的滚了下来,滚到底趴在地上。
两个恶警赶上来拖起我就往外跑,到门外转化者也帮忙往外抬,一直抬到晾衣场,强行把我铐在了晾衣场的铁管子上冷冻。由于天气太冷,下午换了一名转化者看着我。晚上恶警黄海雁又把我铐在队长厕所的暖气管上,夜里值班队长又把我铐在队长值班室的暖气管上。第二天早上再次把我铐到队长厕所的暖气管上。我全身疼痛难忍,手被铐的冻的肿老高,队长上班后,恶警黄海雁又来逼我去出操,直到我违心的答应才打开手铐,结果又叫我上水房,指派转化者“做工作”。由于行走十分困难,去食堂吃饭都要人搀扶,晚上扶我上床的时候,我要翻身却怎么也翻不过去,沈钥(大连人)帮我翻过身,她哭了……我的全身、脸、下颏,青一块紫一块的,很多学员见了都很痛心。
恶警黄海雁不但从肉体上残酷折磨我,还从精神上进行摧残,向学员造谣说我儿子不尖,缺心眼儿。好多学员问我儿子多大,我说我只有一个女儿,谎言不攻自破。关于这件事和在小号遭受迫害的经过,我给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写了三封信,第三封信里还装着我给丈夫的信。
12月份,马三家教养院强制洗脑进入高潮,辽宁省“帮教团”住进马三家。一天下午,室长叫我,我被领到队长厕所,有两个转化者等在那里,我和她们辩解。晚饭后,恶警黄海雁把我带到东侧楼梯口,铐在了暖气管上。过了一会儿,恶警黄海雁说:“不行,得给你换个地方。”又把我带到队长厕所,几个恶警和转化者强行把我往暖气管的横头上高吊,另外的暖气管上还吊着坚定的大法弟子安秀芬。夜里三点多钟,四防人员来解铐让我上厕所,我的手腕被卡出了血,把吊铐我时一名学员给塞垫的手帕都弄上了血。
张云霞被恶警王晓峰在一楼吊了两天,回来后走路困难,吃饭上厕所都得搀扶,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刘艳文被连捆带吊躺在床上输液,几天就花了五百多元钱。
在压力面前我违心的向邪恶妥协了。2003年的一天,我写了声明交上,恶警黄海雁和几个转化者在队长寝室把我高吊,只能脚尖着地,时间一长我又受不了了。叫我写保证书我没写。恶警黄海雁召集三分队所有学员,叫我当着学员的面把声明撕了。中午学员都去吃饭,我没有一点吃饭的心思,没去吃饭,回想起自从非法判劳教以来被恶警黄海雁逼迫所做的一件件有损大法的言行,真是生不如死。我拼死反迫害,恶警王晓峰说:“把她吊到楼下去,就是吊张云霞的地方。” 我被几个恶警和转化者强行吊在了楼下暖气管的横头上。
2003年7月,我不出操,恶警黄海雁把我关到队长厕所的旮旯里。早饭后去,晚十点回寝室。臊臭味熏得我吃不下饭。恶警黄海雁叫学员给我灌食,就这样无奈我又回室了。8月中旬,不出操又一次被弄到队长厕所的旮旯里。恶警黄海雁不让我睡觉,白天黑夜站着,转化者轮流看着我。二十天后才叫我晚上十点回教室讲台上去睡觉,早晨不到四点就起来。恶警王晓峰又强迫我晚上九点从队长厕所回来到走廊再站到十二点,挨冷受冻在走廊里站了十几天又回到队长厕所旮旯站着,因为队长厕所里又搁了别的分队的坚定的大法弟子,队长厕所里外整年都没断过人。
由于长期站立双腿肿得十分厉害,看我的学员曾经当过医生,她用手指按了按我的腿说:“都充血了,毛细血管破裂了。”她把这事报告了大队长,恶警黄海雁又叫我坐小凳。长期冷冻加上精神上的摧残,我绝食了(这里还有孙娟、方彩霞,已绝食一个多月了,恶警石宇每天叫转化学员给她灌食)。恶警黄海雁把我弄到综合楼,下午又把我弄到水房,又弄到队长值班室,几个转化者强行给我灌食,灌完后又把我拖到一搂,铁门上挂着“新生隔离区”的牌子,我被拖到挨铁门的一个号里,晚上恶警黄海雁端来冲好的奶粉叫转化者给我灌,我被呛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晚上九点之后回室睡觉,早晨不到四点起来。对面号里关的是2002年12月强制洗脑时胳膊被吊折的学员,上厕所都得两个人拖,长期卧床双腿不好使,根本站不起来。
这里有专门灌食的恶警曹狱医,一天一个转化者给我插管灌食,灌一小盆玉米粥就三十元。晚上被这个转化者插管灌出了血,一个晚上都在不停的吐血。恶警黄海雁还是不放过我,继续插管灌食。由于多日灌玉米粥加水,我上厕所次数增多。恶警黄海雁说我有病得去医院检查,我说没病,是你们灌食灌的。我被强行拖上车,到了马三家医院我下不了车,又被拖进医院。恶警黄海雁开了检查单,要验血我不配合,被强行抽了血;又要化验尿我不配合,恶警黄海雁钻到厕所里使劲拽我,看我的转化者从外面使劲推我,她们没拽动。走廊里行人不断,恶警黄海雁只好作罢。回到教养院后,把我的双手背铐,整天插着管灌食,(大连的王岩层多次被这样灌食,最后被迫害致死)恶警黄海雁说你不检查钱也花了,花了一百多,后来又说是二百多。晚上不让我上楼,铺上草垫就地躺着。双手背铐怎么也不得劲,我答应了吃饭。手铐打开后,恶警黄海雁又叫几个转化者给我念攻击大法的书,我正念抵制。她们又把我抬到晾衣场冷冻。天气太冷了,她们穿着大衣,围着围巾,一个小时一换。中午我也没吃饭。二大队学员来晾衣场收衣服,才把我弄回楼下。
第二天晚上说回室,刚上楼,恶警黄海雁、王淑征领着“帮教团”的恶警在此等候,又把我弄到综合楼,进屋后才知道他们是本溪的,对我强制洗脑。他们叫我抱轮我不抱,叫我打坐我不配合。于是拿出布带把我的双腿强行盘上后捆紧,把我的左手拧过去和右手铐在一起,把我的脖子用布带缠紧摁着头绑在双腿上,想抬头都抬不起,时间一长疼痛难忍,两脚发黑。我叫她们放开我,恶警拿出“五书”叫我抄,我又妥协了。松开后腿肿得老高,全身不敢动。一恶警狠狠的说:“只要你反弹,就给你回炉!”
一天早晨我不出操,又被弄回综合楼,这时帮教日期已过,几天后又被弄回队长厕所。我在外面,里面是两次被“帮教团”捆绑后被弄到晾衣场冷冻,又弄到队长厕所里的毛玉兰,三个转化学员看着她。毛玉兰的腿肿得蹲下都困难。过年那天恶警黄海雁才叫我回室和学员一起过年,正月初八一早又被弄到队长厕所。不知有多少大法学员遭受这臊臭熏染,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在小号、楼梯口、楼下“新生隔离区”、库房、晾衣厂、三角屋、教研室、队长寝室、队长值班室、水房、综合楼等地遭受残酷折磨……
2004年2月5日是我非法劳教三年期满的日子,那时我还在队长厕所里受折磨,毛玉兰期满走了,我又被弄到里面的旮旯处。数日后我又被弄到教研室后墙根处冷冻。转化者告诉我刘艳文回家了,她被超期关押了半年。
家里人多次来接见,恶警黄海雁把我划为严管对象不许接见。我回室后,一天中午吃饭回来,几个恶警在走廊里搜身。我走到恶警黄海雁跟前说:“队长,你给我加期多长?”她边搜身边说:“你也不参加劳动,呆着吧,共产党有的是粮食!”5月份,一次开周小结会我不参加,被弄到水房,恶警黄海雁问:“你还想过不想过日子?”我说:“我从来都没说不过。”我被拖到队长值班室,恶警黄海雁把我骗到综合楼小号,双手背铐。小号杨队长说:“现在小号比以前强多了,地上铺草垫,比铁椅子可强。”我说:“怎么强还不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个大法弟子绝食,小号恶警天天灌。另一小号大法弟子喊:“队长,我口渴,给点水喝不行吗?”小号恶警不搭理。小号里一个60多岁的大法弟子整天喊着要见所长,遭到杨队长毒打,并说:“你这老太太是不是想升级!”我在小号里被铐了十天,5月13日那天,恶警黄海雁来到小号边打开手铐边说:“给你加期两个月。”我善意的劝说:“队长,你这样做对你没什么好处,你会后悔的,希望你能善待大法弟子。”恶警黄海雁却说:“我不怕下地狱,我自己愿意下地狱!”
回室后,恶警黄海雁告诉学员不许和我说话,并扬言:“谁和周雅娟说话就会给谁加期。”以前在开周小结会时,恶警黄海雁经常和学员说,明慧网上登她打大法弟子五天五宿的事,问学员们信不信,说她那么瘦可能吗?打人还分胖瘦,真是强词夺理。一次在罚站时,恶警黄海雁问我,明慧网上登她用电棍把田绍艳(葫芦岛绥中人)前胸烙坏的事问我信不信?我想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超期关押又不让家属接见,家里人非常着急。丈夫怕我在教养院被恶警迫害死,花钱托人才让接见。2004年9月24日,我被放回家,恶警黄海雁又朝我丈夫要了一千四百元。我被非法关押了三年零六个半月,在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了三年零四个月,给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公爹由于着急上火眼睛出了毛病,在县医院做手术花了一千多元,在乡医院做肾手术花了四百多元,孩子想我想得夜里蒙上被子哭……
几年来给我家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丈夫因照顾老人和孩子不能出外打工,而在家里一年也收入不了多少。而省吃俭用卖苦力挣点钱竟被邪恶之徒勒索。我炼功为的是祛病健身做好人,竟遭如此迫害,我的人权在哪里?我的信仰自由又在哪里?
(注:文中提到的大法弟子杨景芝、王岩已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