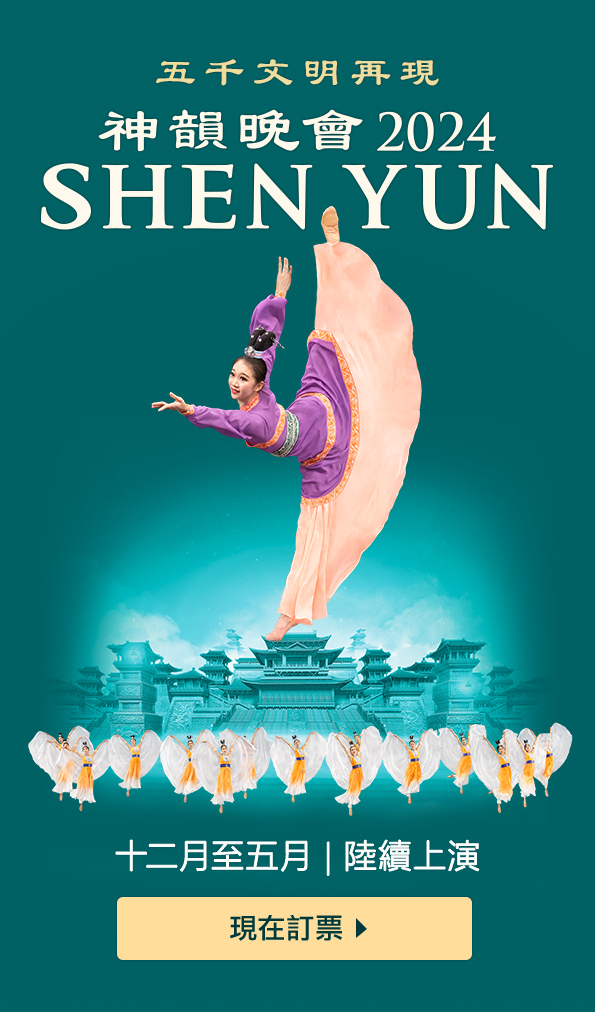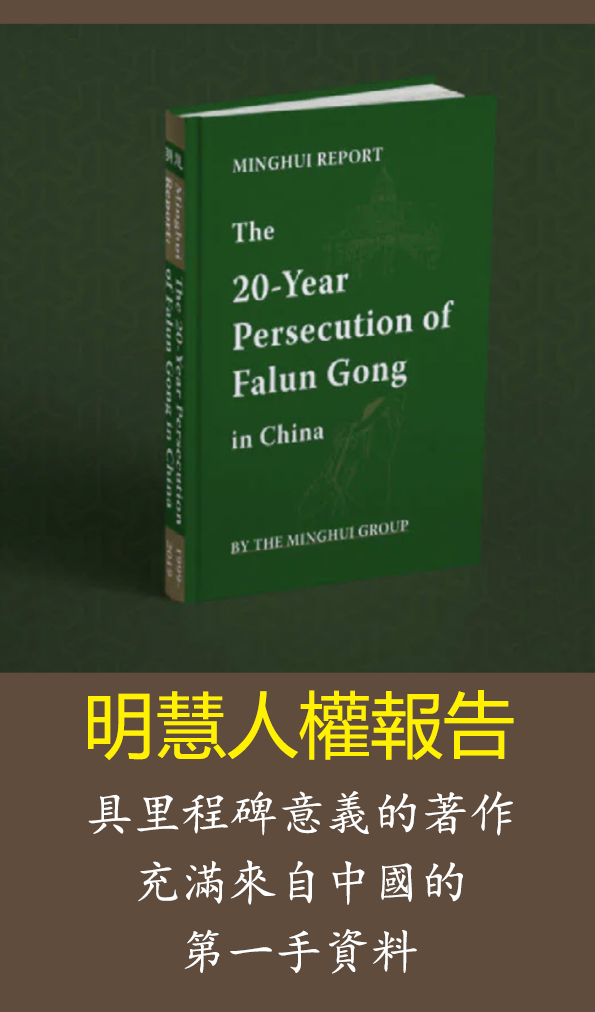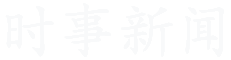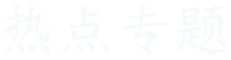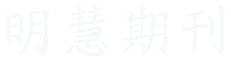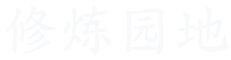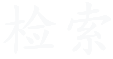河南法轮功学员:我所亲历的这场迫害
7.22河南省委前反映法轮功真象
话还得往前提。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群众和平上访以后,我们就断断续续地得到一些消息,有一些个别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干扰修炼的。那时候在炼功点上,或者是功友之间的交流中,大家总感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功法是不可能受到迫害的,何况法轮功走得这么正,这么光明磊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反对的。但是,面对干扰,大家也都在心里认为这是政府对我们尚未全面了解,法轮功是不可能受到打压的。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只是炼功,于己于人都没害处的。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大家又有一个同感,如果法轮功一旦受到不公的对待,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要向政府说说清楚的。
1999年7.20开始了大逮捕,很多省、市辅导站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失去了自由,7月22日凌晨,功友们都到河南省委去反映情况。我上午十一点左右到达省委附近时,老远就听到广播喇叭在宣传有关社会治安、社会稳定和扰乱社会治安的处罚之类的东西。接着是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大马路上来回跑着,喊着号子。而从不同地市赶来的大法弟子们大都在马路边上,当然没有人组织。大多数人的表情是困惑心酸的。忽然,看到两三个警察在围打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士。接着,又有一个年轻男子被警察反剪着双臂带走了。而法轮功弟子则被警察们连围带引地关进了一所小学校里。大门是落了锁的,只允许人进来,不允许人出去。而教室的门上却早已贴上了不同地市的名称,但是大家都未进教室,在操场上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中午时分,我们那一地区的人进了教室,等着和有关人员见面,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一个自称是省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讲了一通话之后走了,他不外乎说一些集众闹事、非法组织一类的话。再就是让大家发言。我联想起4.25以来大法受到的不公平及当时的情况,站起来说:“对待法轮功的政策不是我们地委拿的,也不是河南省委拿的。但是,这样对待法轮功是不适宜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们应享有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有信仰的自由。”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是很难理解中国实际的人权状况的,在强权政治的高压下,所有和最高集团不一致的言行,都是被打击的。同时,这种打击行为,会被赋予“秉承国家、民族的使命”,很快地由政府职能部门行使着,可以对任何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对法轮功的打压来自最上层。因为,中央的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下午三点左右,校园内的广播上已经开始播放所谓的民政部、公安部等联合“取缔”法轮功的公告。当天的上访就这样不了了之地在他们事先做好的布置下,全部把我们从省会拉了回来。
回来时已是晚上九点左右,其他功友被统计后由当地派出所接走,而我与另两名则被直接由警车带到了市政保大队。政保大队的副队长正开始给我做笔录,他问:“有一次在××对面那个棚里开会你去了没有?”我说没去。他说:“那天,我们在车里录的像,那个高个子的怎么不是你?”我说我确实没去。另一人说:“在×中练功点上你去了没有?”我说我去了。他说:“我当时在后面坐,你念的还挺带劲呢。”我才意识到:这帮子人早就对我们开始了秘密侦察,这场打压肯定是预谋已久了。当夜,我们三人就在院子里被关了一宿,第二天中午,由单位领导把我接了回去。出去时,还要签一份保证不上访的保证书。
因上访被关北京看守所糊纸盒
99年10月,我因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到看守所。看守所都是大筒子房,每间有三十平米,厕所在房间角落里。每房一般都要有二十多人。睡的是木板做成的通铺,即使是人挤人,一头一个也睡不下这么多人,所以有一些人就睡在通铺与墙之间仅有的空隙里。通常在看守所内做的活是糊纸盒(打针用的药盒)。由号头分成四个组。对号头和狱警来说,干活是他们管理犯人的一种手段,更是他们榨取犯人油水的绝好途径。我所在的小组相对来说比较慢,就成了号头责骂的对象。进入寒冬,号里根本没有玻璃或其它防风用的物品,里外温度几乎是一样。我的两只手被冻烂。时不时的晚上值班要加班干活,有时浆糊都结了冰,还要用手指去涂抹。一日三餐清汤寡水,早上一个馒头和一碗能见底的稀饭,晚上一个馒头和一碗水煮的稀白、红萝卜、白菜、菠菜咸汤,中午是一顿面条,也就是一两多面吧。吃完饭不要说半饱,也只是当时感觉不那么饿了。有时为了找一点吃饱了的感觉,就赶快把饭吃完,以使得空荡荡的胃有那么一丝感觉,随后仍然是饥饿难耐。
家里亲人为我四处奔波,多方托人,最后花了一万五千块钱算是给我跑了一个“劳教三年,所外执行”。我在看守所内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出狱时,又要向公安局交一万块钱押金。同时,610办公室通知学校,不准上课,工资停发,每月三百块钱生活费。
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给女儿过生日,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区政保大队的李××、黄××等五、六人到我家里来抄家,搜出了几份资料和我以前写的一点东西,我和妻子二人一起被带走了。在政保大队,李××、黄××二人对我连打带骂,二人一起下手捆绑我。第一次没有绑住,李××照我头上就是两拳,口里还骂。把我绑起来后,黄××用脚照我头上就跺,李××也是一边骂着一边打我的耳光。指着我以前给家人写的为什么要到北京的信:“放在以前你这就是反革命!”然后又过来照我头上打。打了一阵后,他们坐下来看我在地上痛苦的翻身抽动。这两个人捆我时绳杀的狠,我感到两臂撕裂似的疼。我使劲忍着,憋得浑身是汗,佝偻着身子来回抽动以缓解疼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黄××动手给我解绳,看李××的表情,好象还不该解似的。然后,黄××拽着我的手使劲晃动。后来到了劳教所我才听说绳杀的狠时能把胳膊捆残,我才想起黄是怕把我的胳膊捆残了要担责任才帮我活动胳膊的。
然后,就把我送进了拘留所。一次河南省公安厅的一名什么处长来本市,把我提出来看我的态度。从他们说的话语中,我知道是想让我替他们工作,做他们的内线,他们拿着纸让我写认识,我说不用写了。在拘留所关了二十多天后,就把我送到开封劳教所。
开封劳教所的非人奴役
在开封劳教所教育队呆了一个多月被分到三大队。三大队距劳教所有十多里,按其他劳教人员的说法,这里是天高皇帝远。大队长反复强调的则是:这里是三大队。那意思是很明白的,在这里就得遵从这里的规矩,无条件地服从警察。
三大队一百多号人,来回也就一两个法轮功学员。我被分到灯泡车间检验灯泡,另一名则被分到外工队。而且明确告知不准我们有任何接触,同时,又找了两名劳教人员负责包夹我。按警察队长的说法,法轮功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在监视之下,不要说出工的时间,即使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人员包夹,本来就失去自由的人,还要对我们做进一步的限制。
在三大队我感到最令人窒息的就是在那种暗无天日环境下的劳役折磨。早上六点起床,七点进车间,晚上六点出车间,有时警察队长还要随意地延长时间。车间里如果不亮灯,和夜晚没什么两样。这种长期见不到自然光源的工作环境都能给人的心里笼上一层阴影。夏天还比较好些,能见到点天光,到了冬天,进出车间所能见到的只有星星。厕所在车间里面。只有午饭时才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出来见见阳光。外界的一切几乎都是隔绝的。生活区的围墙有两层楼高,这里确实是禁闭了一切。晚上收工后,大多时间是队长包揽的一些手工活,大多还需要两个多小时。碰上手头慢的,或新来的劳教人员,有时几乎要干上一个通宵。我开始去的个把月时间,活都要干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完成。冬天是根本就洗不上澡的,天气暖和时洗澡就在院里的水池旁,找一个水桶,找一个脸盆。为什么找水桶呢?水流的很慢,有时接一桶水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卫生确实很差,三大队在城外,积水有时排不出去,雨水多时,厕所里的蛆虫就漂了上来。有时,吃着饭,都能见到,蛆从蹲着的脚边爬过来。甚至有一天早上打饭时,从稀饭锅里打出一只死老鼠来。
在劳教所我一直在思考,对法轮功进行这场迫害的元凶究竟是谁,是谁在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展开这么恶毒的迫害。这么大范围,系统、彻底地针对一群只为做好人的人进行打击,而且打着国家的旗号,操纵整个政府。以前,我看到过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考察的录像,也看到过其他大中城市对大法正面公正的报道,朱镕基总理4.25接见法轮功时曾有过正确的评价。然而这一切怎么一夜之间就翻过来了?这一切肯定来自于最上层,而且不可能是政治局常委的集体决策,因为法轮功走的路太正了,他改变修炼人的人心向更高更完美的境界发展,有一点良知的人他就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认可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作用。那么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人就只能是那个把国人都看成是自己的附庸,自己拥有着国家的一切权力,不允许别人比自己高明,更不容许一个人能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这个人的妒忌心很强,这是他发动这一切迫害的出发点。这就是当时那个把国家主席、党中央书记、军委主席等权力集于一身的“核心”江泽民,而整个政治局常务则是被挟制了。
三大队的生活是很苦的,许多农村劳教人员都说:“吃的还不如我们家里的猪吃的好呢。”完不成任务时还得受罚;皮管、上绳、顶墙、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哪个劳教人员完不成任务,警察队长让组长想办法,组长也就是看守所的号头。因为我所在的组以前也曾有过两个大法弟子,那个号头对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但当队长背地指使他时,或许用什么减期做诱饵时,他就会一反常态。有几次他指使包夹我的人员在夜里十二点之前不准我睡觉。到后来,他又指使两人对我谩骂,反正是怎么难听怎么骂。当我和这些人分手时,他们也都表示没办法,有人指使。当然,我不会记恨他们。我所接触到的被关押的人中,极少有对我恶意打骂的,但是,在有警察怂恿时,情况就会突变。
面对这肮脏的环境,我无奈,但是,我不能顺从警察的安排。我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本性告诉我,要有勇气面对现实不能说假话,不能昧良心。有一天大队长和我谈话,谈得很微妙,既不失他的身份,又让我顺从他,既能得到政绩,同时也表示了对我的关心。他说:“坚持一个什么东西,那要看怎么坚持,你完全可以走另外的路。我又没有要求你放弃,为什么不换一条路呢。”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说假话,先回家。我说:“我怎么认识的就怎么做,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我别无选择,何况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昧良心说法轮功是X教,然后躲在家里偷着炼,那社会上的人谁都会认为是这样了,因为你自己都承认了嘛。更何况法轮功讲真善忍,我要说假话本身就不真了。”他又提我的家人和孩子,我说:“我是对得起孩子的,她的父母(我的爱人也被劳教了)在该他们说真话的时候,他们说了,我不能让孩子长大后,在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看不起她的父母,她会为她的父母感到骄傲的。我坚信法轮功有正过来的时候。”
他说;“你怎么认识法轮功,按你的说法是受迫害的?”我说:“我认为这是中央极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了政府迫害法轮功。”他说:“照你说这个人权力还很大呢。”我说;“是,没有权力他还搞不成呢。总理的批示都能被压下,总理的意见都会被否决,总理可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他还说:“国家不让练,你练就是不爱国。”我说:“不对,国家和政府不是一个概念,是现在的政府不让练。不能说政府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刘少奇不是死在开封吗?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发动的吗?”他说:“不管怎么样说,把你送到劳教所你就是有错。”
我准备写一份东西,彻底否认施加在我身上的一切迫害。我列了提纲,中间写到我不配合劳教所不是给三大队及三大队的队长找麻烦,也不是让开封劳教所下不来台阶,而是对少数当权者迫害法轮功的抗议。这份提纲被搜走。再后来,由于我抵制警察大队长让我顶墙的惩罚,便把我调到了四大队。
四大队设在开封市磷肥厂。在三大队我就听说过四大队的残酷。我的一个功友从四大队调到三大队来,给我说:“一进四大队便把我呈大字形铐在铁床上,两手铐在上铺的床柜上,晚上值班的轮替换着看着不让我睡,一闭眼就打,主要是拧腿。只在黎明时准许睡一个多小时,白天还要装二十五吨的磷肥。有几次四大队政委、大队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快受不了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慢慢就适应了。我确实承受不住了,两腿肿得都穿不上棉裤,铐了我二十一天……”后来这个人按照警察的要求“转化”放弃修炼后,还被拉去到大学、军队、工厂向人们诬蔑法轮功,而他所经历的一切迫害却不可能再提。是什么样邪恶的力量使得一个正常的人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能够认贼作父地颂扬扭曲了自己灵魂的恶魔。这就是最没有人性的“洗脑”,这就是中国劳教所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成果!我亲眼目睹他的“转化”过程,写揭批法轮功材料时的苦闷、烦恼、痛苦,当他徘徊时,不想昧着良心说假话时,大队长的一句“不写还送四大队”的恐吓在他心中能起到的份量可想而知。
在劳教所举办的“洗脑”班上,我还见到一名曾在四大队承受不了超强度的劳动而违心妥协、后又走回来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警察运用的各种方法都未能动摇他的心,可是当四大队大队长找他谈话说:“不转咱回去再练练”时,他就有点谈虎色变,当他真正得知坚持修炼的都要送四大队,而且包夹他的犯人也都换上四大队的人员时,他就又走向了所谓“转化”。
我是下午五点左右进入四大队干活的仓库的。大队长梁洪涛笑哈哈地说:“早就听说了,先干干试试。”进入车间,便有组长给找铁锹。四大队的磷肥包装完全是人工。一个人撑着磷肥袋放在磅上,两个人在磅前一替一锹地装。装满一百斤后就由撑袋(称磅长)的甩到身后,然后有人手提包机去缝袋口,尔后用车拉走。干到晚上将近七点,梁洪涛过来,我说:“我从早上七点进车间(三大队进车间的时间)现在干到这么晚,得干多长时间?他说:“叫你干你就干。”我说:“要这样,我就不干。”他说:“我命令你干。”我把铁锹一丢说:“不干。”他说:“你出来。”
这时六七个组长都围了过来,其中一个外号叫老猫的大声吆喝:“比你硬的老子见多了,欠揍。”其它几人也都随声附和。这时大队长说:“你干不干?把他带过去再试一次。”几个人就把我拉进车间,大队长梁洪涛在后边装模作样地喊了一声:“不要动他。”我已经清楚梁洪涛就是想让这几个人把我拉开,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打我。
可想而知,我会遇到什么,这几个人是不由分说,把我撂倒在地,不分地方的在我身上乱跺乱踢。尔后,一个组长让人脱下一只鞋来,用鞋帮照着我的脚底狠打一下,然后换一只脚,又是狠打一下。我就感到两脚钻心地疼,脚底板迅速就肿了起来。回来时已经是一瘸一拐地走不成路了。梁洪涛问:“干不干?”我说:“不干。”他说:“铐起来。”收工后,梁把我喊到他屋里说:“要干就干,不干天天铐着。”
我初去时磷肥一天要装五十吨,一百斤的袋,那就是一千袋。两个人装,两个人力量要大的话,一袋就是七八锹,力量弱一些,那就要十三四锹。平均十锹算,一天要装五千锹。这还要除去料不好时,用镐去掘料,把磷肥板结形成的疙瘩清出去。有时光掘料一天累计也要用去三四个小时。装袋的速度是极快的,不能有丝毫的放松,稍一慢,撑袋子的就要骂,更多的时候是打。因为撑袋的力量都要找最强的,完成任务的快慢重点在他这,袋甩得快,动作麻利,任务完成的早些,减期就高些。同时队里的一些优惠政策又都有倾斜给他们一些,如有时可多加一块馍。完不成时,经常落后的撑袋者就要受惩罚。一些警察或组长看到哪个组落后一些,过去就打,撑袋子的直接挨打,那么他打装袋的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规矩不知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装袋子的拼命地装,撑袋的不住口里还要叫“快、快、再快点。”有时料不好时,撑袋的就丢下袋子,照着装袋的就打,要么用脚,要么用锹把,有时拾起磷肥疙瘩就砸,或者操起镐掘一阵料。因为他不打人,装的慢一点,他就要挨打。所以打人的情景是随时可见的。每个人都是在拼了命地干活,只有那些组长们,他们是队长得力的帮手,出外找碴。不要说解手,稍微慢一点喝磅头上放的水都要挨骂,或明确要求不准喝。
两天下来,我的手打了二十几个泡,肘关节处撕裂似的疼,躺在床上翻不过来身。我初去,活又重,平生又没干过多重的活。干到晚上六点左右时,一数还有十五、六吨没装。我知道原因出在我这,尽管我几乎拿不起锹来,听着一组人的咒骂,我只有竭尽最后一点力气苦撑着。和我一起装的人一边骂着,一边不时地砸过来一块磷肥疙瘩。这时组长过来吆喝了一阵,把我拉在一边说:“找个人装装如何,一吨十块钱。”我说什么呢?我连说话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我确实装不下去了。心想,一下子干这么重的活不行,适应两天可能就过去了,再一算还有几百块钱在帐面上,找就找吧。后来经过交涉,找一个人给我装,一吨五块钱。
这远远不是两天就能适应的问题,当一个人的力量几乎被用尽,而又没有休养和食物补充,每天都是这样竭尽全力地硬撑,一个月内就甭提适应的事。当时,我唯一依靠的就是一点信念:我不能倒下去,能活一秒钟,我就坚持一秒钟。这种雇人装袋的事也就那么几天,我知道,这种交易是肮脏的,是劳教所的黑暗滋生的这种交易,当然不能去适应,何况这点钱都是亲戚朋友接济的。每天都是十多个小时的劳动,上午九点多钟我就感到力量不济。两只手打的泡已经溃脓,磷肥沾上火烧似的疼痛。
一次,料不好,我和一位年岁大些的人一块装。装到上午十一点多钟时才只装了十多吨,队长转了一圈就喊,上午收工时必须都得装到二十吨,要不下午没法干。我们这组是最慢的,一个组长过来照着撑袋的就是几三角带,然后又去狠命地抽另一个装袋的。我知道,这是打给我看。因为我和大队长梁洪涛多次提过,他们打人太厉害,也太不应该。大队长给我说:“不打咋办?这活都是打出来的。”我说打人不是办法,这不能成为打人的借口。我多次明确表示,迫害法轮功不让我们说话。我所遇到的一切,只要让我说,只要我有一支笔,我都会说出去。当组长在队长给他们开会时,就有个组长提出,法轮功能不能打,队长明确表示不能打。虽说不能打法轮功,可与法轮功一块干活的就免不了了。所以很多时候打他们,就是在给我们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拼命地干活。被打的人直喊:“法轮功老弟,求求你快点。”尽管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在队长和组长看来,还是不够快。
说起打人,劳教所可真是一套一套的。他们对付起法轮功学员也是穷其所能。为了防止大法弟子互相交流,这些组长就狠命地打包夹我们的人员。时间长了,有时包夹人员对我们很同情,多少能睁只眼闭只眼。可是不行,一旦被组长发现了,就会被关到屋里痛打一顿。一次包夹我的一个人员被叫走,我意识到是去打他,听到屋里有响动,我推门就进去了。这时一个组长正举起木棍往他臀部上打,那人趴在地上不住地求饶。组长见我进来,不打了,另几个则说:“队长见了说我咋办?连你们几个都看不住。”我只能说:“你们别打他了,我们以后不说话就是了。”
活确实很重,按劳教人员的说法,四大队进来的人一般都是一年两年的,三年的极少。因为活太重,干一年出去还能恢复过来,连续干三年,怕把人弄废了。也确实,四大队的劳教人员的期限也多是一年两年的。对劳教人员来说用的最费的是手套和鞋。一对手套交替着戴也就是一个星期。就这样,几乎整个手掌都磨起了老茧。开始干活前五分钟左右,手指根本弯不过来,只有干一会儿活,活动开了,才能握住锹把。收工后冲洗时,因过了一段时间,手又不能拧毛巾了,只能将就着用手捂一捂。料不好时,需要用脚蹬铁锹,所以也是很快就把鞋底蹬断。铁锹也是二十多天就要换一把。有时厂方不给及时提供铁锹,就只有拿着破铁锹了。这样重的活,伙食也好不到哪去,每月60元的生活费就全包了。有一次警察队长说:“人的潜力真是大啊,一顿顶多就是俩馍,却能干这么重的活,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就是这样奴役人的。我在前几个月基本上一个月瘦十斤肉。出来一年后,我的指关节才算完全恢复(没有恢复前双手指关节是握住伸不开,伸开握不住)。
三伏天,仓库里面象个小蒸笼,天气预报最高温度三十八九度,仓库里的磷肥也有一定的温度(刚生产出来的,还湿碌碌的,在仓库有个干燥过程,磷肥的化学反应尚未全部进行完,是有温度的)。大队长在出工时却坚持不减任务(当时每天装四十五吨)。前几天就有几人中暑昏倒的。大法弟子老邓,五十七岁,也是中暑昏倒的。得到的救助就是抬到通风的地方,用凉水冲冲头。上午中暑,下午照样出工。
母亲的悲痛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劳教所为了逼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特地建了一个洗脑班。洗脑班上从军训到看诽谤法轮功的录象,还有邀请什么和尚、心理医生、演讲家之类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还举行了所谓的亲属帮教。一次我家里人来看我,队长们给我家的亲属谈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第二天专门把我和母亲关在了一个房间,妈妈劝了我一阵看我没有丝毫动摇的意识,一下子跪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明白了劳教所的卑鄙用心。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母跪在地上,我心如刀绞。我说:“妈,你起来。”母亲说:“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跪这不起来。”母亲哭着说:“你是谁呀,你是我的老祖宗吗?我咋就得跪着你……”母亲悲痛欲绝,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我说:“妈,等我出去后,我就回家。不是我不要家,是政府把我关到这里的,我没错。”母亲说:“你不转化,你怎么能回家。人家说了,不转化的到期也不让走,说要送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母亲将近七十岁了,一生含辛茹苦,孩子是她的希望和寄托,她曾为自己的孩子自豪过。当孩子成为阶下囚时,她的心怎能不痛?妈妈哭着说:“你知道这两年咱家咋过的。你和孩子的妈都走了,剩下个小孙女还不到十岁。你爸成天唉声叹气的,从你开始出事,他都很少说话。家里四处托人跑你的事,人家都说,你不转化谁也没办法,杀人放火还能说个情,就法轮功,谁也不敢表态。儿啊,你就转化吧。”我噙着泪说:“不,妈,我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我今天就是不低这个头。”就在母子俩痛苦不堪的时候,一个警察悄悄推开门,端着照相机来找他需要的镜头……
在中国,一个敢于坚持信仰、反对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会遭受这种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亲属孩子都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是一亿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吗?牵扯了多少老百姓的心?为什么就要因为江泽民一个人的晦暗嫉妒心,就逼着全国上下的人说假话、跟着跑呢?每个人都在这中间起着作用啊,是坚持正义还是怯懦畏缩、沽名钓誉?人活着是要有人格的。
到期后,单位派人把我接回来。先不回家直接送到当地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一个副局长给我说:“今天上午公安局、610办公室、咱局里,几个单位开了一个会专门说你的问题。这几年劳教你谈谈你的认识”。我说:“第一我不转化,这是我的信仰问题。”七八个人在屋子里,其中一人一听我说这话赶快拿起笔来。事后,原说局里把我的态度往上作了汇报,准备把我继续关押。610办公室作出三条决定:一不准讲课,到后勤干杂活;二工资执行九九年的工资标准;三不得离开学校,随时等候传唤。
我只是亿万法轮功学员中的一员,这四年多来给我造成的迫害是刻骨铭心的。迫害还在进行着,我把我的情况写出来,希望能为揭露邪恶、制止迫害尽一点绵薄之力,如果能在起诉江泽民及其帮凶上起到一点作用,我是非常高兴的。